难以释怀的隔世情怀-博奥官方网站

婆,是沉在我心里的童年情怀,弥漫着乡土,储存着拮据的幸福。
那间婆居住了一生,低矮破旧的土墙围起来的门户里,人最多时达到8口,如今,生离死别,时光变迁,陈旧的屋檐下就剩婆一人了。吃饭时,婆端出小方桌,多拿一双碗筷摆在对面,给离世的爷爷说,快吃吧。她看着碗低语,“不知道你在阎王爷那里报道了没有,报不上名就领不到饭票,领不到饭票就没饭吃。想着你饿了,快吃吧。”
婆生活在农村,含辛茹苦抚养六个儿女长大成人,那些经受过得辛苦,虽从不言说,却沧桑了面庞,弯曲的脊背烙印着生活曾有的艰辛,两鬓的银丝苍白着仅剩的耄耋光阴。
随着儿女们一个个成家立业,苦尽甘来,日子自然是越过越好。可幸福不长,爷爷因病去世,突然失去伴随自己半个世纪的另一半,像房子拆去了半边,身体瘫痪了半边。儿女们让她搬到二伯家住,以释伤怀,她坚决不肯。睹物思人,那座宅子有她一生的细枝末节,是他生命中无法割舍的生存空间,要让她离去,如同将她思想的根系从泥土里拔起,她又怎肯。
有天,父亲让我去买成人尿不湿,说是给婆用,我忽然心酸,不敢想象她在病床上的模样。我挑最贵的买了五大包,再给婆买了小孩吃的零食,一起提着回老家,心里沉甸甸的。路上,听父亲说婆意识糊涂了,经常不认识人,有时对着镜子跟里面的老太婆聊天,问她有几个儿子几个孙子,是否都在身边。倒是身体还行,能吃能睡的。
进门前,父亲掏了张百元钞票,让我给婆。冰冷潮湿的空气,夹杂着一阵尿的酸骚气味,姑姑说婆像孩子一般不听话。婆面无表情的坐在一堆人中间,有几个人问她认不认识自己,她纷纷摇头。我提高嗓门说,“婆,我来看你了。”婆抬头看了我一眼,“琨琨娃,你咋回来了?哎呦,琨琨娃回来了,真的回来了。”姑姑开玩笑说,身边伺候你的人都不认识了,就记得不长回来看你的孙女和二儿子。我拆开一包零食取了一颗给婆,她迅速的塞到嘴里,没有牙齿支撑的口腔慢慢蠕动,心满意足的享受着小饼干融化在嘴里的滋味。我塞给她钱时,自己又添了些,众目之下,她把钱藏到被褥里。只要婆开心,在场的每个人心里都是甜的。看着在人群里痴痴呆呆的婆,我心里隐隐作痛,曾经鲜活的生活画面伴着几点泪水静静的滑过心田。
我六个月大时开始吃鸡蛋,雷打不动,每天一个。孩童时,别人问我这么多鸡蛋哪来的,我就说婆在老家给我下的。
儿时的我只是一味心安理得索取,婆听说我爱吃鸡蛋,自己舍不得吃,给我持续供应着。而我,倔强的享受着一个孩子的特权,我知道婆对我好,可不喜欢婆就是不喜欢。好久不见我这个孙女,她总是忍不住用那双粗糙的手抚摸我的脸庞,她抱我时衣服上总能闻到牲口粪便的味道,家里的水太难喝,杯子看着不干净,家里的炕太硬睡不惯,婆睡觉会打呼噜吵我,婆煮的鸡蛋太老,总之,我是一百个不愿意在这里生活。后来,我再来到老家,喝水是甜的,水煮蛋不老不嫩恰到好处,睡觉再也听不到扰人的鼾声。婆悄悄把我叫到一旁,从腰间掏出一团手帕,像剥粽子一样打开,里面裹着的几张零钱,偶尔还有几个淘气的分分钱滚落到地上,我会开心的捡起,婆再塞给我几张,说是村口的小卖部新进了一些小玩意。婆怕我冻着,给炕火中添了把柴火,火势突然旺起,熏得她眼泪直流。我还抱怨盖的被子都是烟熏火燎的气味。我真为那时的自己感到愧疚,一个老太婆为了博得一个小毛孩的欢心,花费了多少心思,怕自己打鼾甚至一夜未眠。
2014年寒冬,情人节那天,婆走了。好在没有病痛的折磨,走的平静又安详,这段银色旅程在子女亲情的润泽中得以善终。比起大多数的农村老太太,婆是幸福的。(张琨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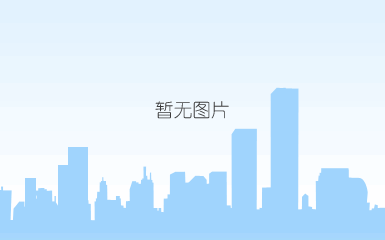




 地址:陕西蒲城县渭北煤化工业园区 邮编:715500 电话:0913-8186000
地址:陕西蒲城县渭北煤化工业园区 邮编:715500 电话:0913-8186000